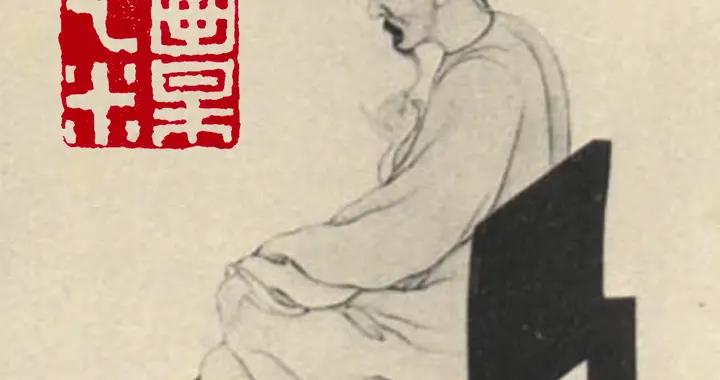西谚有说“魔鬼都藏在细节里”,中国成语有“颊上三毛”,相对于文艺来说,它们有相同的指向,就是在艺术作品中,精彩之处大都藏在细节里,实际上,我们可以把这句话这样理解,学习篆刻,最重要的就是向前辈名家学习那些藏在细节里的精彩。
本文结合奚风的一方普通白文印,说说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方与圆、虚与实。就是这方“画梅乞米”:
(奚冈的“画梅乞米”)
“画梅乞米”的典故我们已经讨论过了(见吴让之“画梅乞米”读印文章),它最早应当始于元朝的王冕,王冕不仅是画家,也是印家,他清贫一生,淡泊名利,曾携妻儿隐居绍兴九里山,以画自给,鬻画换银,过着“画梅乞米”的生活而终无悔意。因此,很多后世艺术家,以“画梅乞米”铭志,以“画梅乞米”自标志趣。
启功先生说:书法中的笔画全是弯的,没有绝对的直线。人人都知道写字要横平竖直,但真要写成平直的,那是很难看的。对于篆刻也是这样,要真把所有的笔画都刻成平直的,那是匠人就可以完成的事情,而不是艺术家的创作方向。因此,我们考察篆刻名家的印,主要是考察它是如何变化的,就让我们看一下这方印里变化丰富的细节:
1、四根横线。这方印印面四字,我们在每个字里都挑出一根横画,认真分析它的细节变化:
(四根横线的变化)
第一根横线是“画”字的顶横,它被处理成方起圆收,基本等粗;第二根横线是“梅”字的中横,它被处理成圆起方收,线条起、运处都较粗,收笔较细;第三根横线是“乞”字的上横,圆起方收,基本等粗;第四根横线是“米”的中横,方起方收,中段膨胀。第三横、第四横的加粗、膨胀是为了使左侧简单的两个字,在文字线条的配重上能与右侧较繁密的两个字对等(实质上,“米”字的竖,“乞”字的下弯都被加粗,起到的也是平衡章法的作用)。
2、两根竖线。我们再挑两根相对独立的竖线,一根是印面右侧“梅”的中竖,一根是印面左侧“米”的中竖。
(印面左右的两根竖线)
显然,这两条竖线都直上直下,但两端的处理并不相同,“梅”字的中竖起笔看不到,收笔却是圆的;“米”的中竖起笔、收笔全部是方的,这又是“方圆互异”的处理。
3、一根曲线。这方印中,四个字,只有一个字带有曲笔,就是“乞”字。遇到曲笔斜线,自然是“取巧写过”这一点不用置疑,为了保证整个字的端方姿态。
(乞字下弯的姿态)
但其中的细节却是值得品味的。首先是起与收的“方圆互异”,起笔是圆起,最后的收笔是方笔;其次,还有两个转折处方与圆的处理:上部一弯外方内圆,下部一弯,内方外圆,细节处变化足够丰富。
4、四个点。这方印中有且只有四个独立的点,就是“米”字的四个点,
(米字四点)
这四个点并不简单:[1]它们四角占位,撑满左下角印面,使印面左下角足够充实;[2]它们姿态各异,方与圆变化丰富;[3]它们两两成对,在姿态上左右呼应。
5、转折处。实际上,这方印中的文字,对称位的转折处差不多都是“方圆互异”的。比如:
(对称位置转折处的方圆互异)
画字的“凵”部左右各有一个转折点,被处理成了一方一圆;中部“田”部两个下角互相对称,也被处理成一方一圆;“梅”字的下部两脚,也有两处对称的转折,除了线条交接处理出来交接笔触感外,也被处理成一圆一方。实际上,“画”字中部“田”的上部两角,也被处理成不同状态,在求异求变化这件事上,作者是穷尽心力的。
以上这些还不是全部。这方印还有值得一说的东西,比如章法上,这方印的四个字,本是天然的两疏两密,由于“画、梅”两字相连,无论用何种字序,这两个字必然相连,或在印面右侧,或在印面上侧,作者改变了“米”字四点的篆法,使全印的章法变成了“三平一变”(或者“三密一疏”)。印面由此变“活”了,因为有了实与虚、疏与密的对比,有了反差,有了视觉差异,也就产生了变化之美。
(芝麻点残破与中部的“红线”)
有了“方圆互异”,不但是使印面充满变化,同时还使印面元素包含了阳刚与阴柔之美,因为方呈现和表达阳刚,而圆呈现和表达阴柔。
但这还不是全部,我们还要看到印面“乞”部红地上的“芝麻点”残破,因为是它们的存在,打破了此处“红地”过于“实”,要破实为虚,又不至于影响与右侧印面的“计白当墨”;我们还要看到印面中部留出的那条宽宽的“红线”,这条“红线”参与了印面章法,使印面左侧变得格外空灵,同时也使印面右侧变得格外充实。而“空灵”与“充实”正是艺术精神的两元(宗白华语)。实际上,这也是赵之谦在《铜鼓书堂集古印谱记》中所说:“盖一聚一散,仍此数颗不坏之宝,成事类然,无足异也。”聚,是密,实际上也是充实,散,是疏,实际上也是空灵。
(【布丁读印】之107,部分图片源自网络,版权归原版权方所有)
作者:谈艺录
来源:今日头条
免责声明:文章/图片来源于互联网。熊猫叶作为化妆品行业信息共享平台,部分内容转自化妆品行业媒体以及网络新闻媒体,仅作传递信息用,不以盈利为目的,并尊重原创,如有涉及版权等问题,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处理。